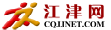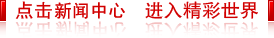一季包谷一春秋
李均敏
春种秋收,包谷也算是印证这个词儿的大众食物。和它有关的记忆,是小时候的岁月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。仿佛又回到了从前,捏营养罐、给包谷苗除草、搬包谷、砍包谷杆……这一系列的农活儿又鲜活地印上脑海。
在我那山高路远的老家,与其他农村一样,都有这样一句俗语:“清明前,好种田。清明后,好种豆。”在清明节前十天左右,新一年的水稻就要撒下田里,一箱一箱的用薄膜盖起来等着发芽了。忙完平秧田、撒秧种的活儿,新一季的包谷也要准备种下地了。
捏营养罐是种包谷的准备工作。一些家禽粪便和着草木灰再添点稀泥,摸起来软软糯糯又黏糊糊的时候,就可以捏出一个个小窝窝头形状的营养罐了。把捏好的营养罐摆得整整齐齐,再在每个罐里放入两颗包谷种,覆上一些松软的泥土,包谷育种就算告一段落了。
在等着包谷种发芽这几天里,爸爸妈妈也没歇着,把需要种包谷的地翻松,等着移栽营养罐。
营养罐是真的名副其实有营养的聚集,这物什营养特别充足,罐里的包谷苗通常都长得特别壮,移栽后存活率也很高,半个月就能长到小腿肚那么高了。这时,除草也是应季的事儿。母亲总喜欢叫上扎小尾辫子的我,拿上小锄头一起去地里除杂草。“人站旁边来,锄头放前面”“隔得近点儿再用力挖”,我一边听“教练”并不熟练的指手画脚指令,一边调整着自己的姿势。然后,就是一声大叫“哪个喊你把包谷苗挖断的?”这样的事故虽然偶尔发生一次,也够气得妈妈七窍生烟了。这时,我心里也暗暗着急,农活小能手的我也有帮倒忙的时候。半天锄头握下来,手掌心就会磨出一个亮晶晶的水泡来,那滋味别提多酸爽了。除草施肥两三轮过后,包谷苗也就渐渐长大了,有些包谷杆长得比两个我叠起来还高,几乎每根包谷杆上面都会挂上一两个带着“头发”的嫩包谷。
烧包谷——儿时不可多得的可口美食。每当包谷开始成熟的时候,附近的包谷地总能看到我转悠的身影,看看哪个能下口了,哪个个头是最大的。偷偷撕开包着的叶子,用指甲掐一下,还冒着浆的嫩包谷就被我搬回家放进灶里了。一边烧火做着饭,一边翻着灶里的包谷,心里别提多美了。烧的包谷总是黑黢黢的,数着粒粒慢慢吃,一排一排地搬下来摆在一起再大口大口吃……感觉真是人间美味。长大以后,也吃过多次烧包谷,却是再没吃出那样的味道来。
吃过了嫩包谷,就期待着撕包谷杆的乐趣了。包谷成熟的时候,正是农历七月份,暑假里最热的那一段时间。背着背篓,走在路上都直冒汗,更别说钻到包谷林里面去搬包谷,衣服裤子都被汗水浸得透透的。包谷长势好的地,搬不了几排就装满一大背篓,沉甸甸地背在背上,又累又热又痒,包谷叶子在脸上身上刮得生疼。我总是一边搬一边吵,为什么种这么大的包谷啊!
砍点水分多点的包谷杆解下渴,算是苦中作乐的开心事了。拿上一把大镰刀,把搬过包谷的杆杆一根一根地齐头砍下来,整齐地堆放在一起,晒干又是上好的起火柴。
爸爸在前面一跟一跟地砍,我跟在后面一根一根地尝。偶有尝到一根水分较多且带甜的包谷杆,就像中大奖一样欣喜若狂,最后,我的背篓里大多装的都是可以啃的包谷杆。妈妈笑骂我偷懒不想干活,却也会暂停手上的活,拿上一截包谷杆啃几口解解渴。
搬回家的包谷,更让我头疼。要把所有的包谷粒一颗一颗抹下来,这可真是个大工程。接下来的几天时间,全家总动员,翻出所有胶鞋来,倒挂着架在板凳脚上,就用这简陋的装备开始“抹包谷”啦。手握一个包谷,用力地往胶鞋底上擦,包谷粒就“刷刷刷”地掉下来了。抹一会儿手就擦得又酸又疼,爸爸妈妈为了调动我和姐姐的积极性,拿出“大贰”(一种纸牌)大家一起参与游戏,输赢都能领到一堆包谷。最后,一家人齐心协力也就把工作干完了。这些抹下的包谷粒再经过几个太阳的翻晒,存仓里,一季包谷就收头了。
我家如此,乡亲们也如此。就这样,山沟里的一度春秋在辛勤的劳作下悄然离去。年年如此,岁岁如此,那些或苦或甜的和包谷关联的趣事装点了我童年的春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