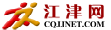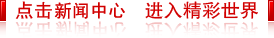登临望乡台
望乡台是老家江津檬子村的最高处。接近台顶的坡级上,依山势而建的建筑旧时是一座庙宇,不过早就成为刘家的住房,人间烟火在一日三餐之际袅袅升起,仰望它与云霄相接。最顶上,是村里的牛棚。生产队大大小小五条牛,全圈养在草棚。
负责喂牛的,是我叔辈,我也随全村人一样,称他“干人”。他是望乡台刘家唯一的儿子。刘家三代人,刘乾佑是个半天不说两句话的老人,妈让我唤他“大爷”。见了我,不说话,只是笑,笑起来眼睛眯起看不到瞳仁。他家里堂屋有一尊观音石像,石像旁总是坐着那个比观音还老的太婆,虽和颜悦色,我却总怕靠近她。刘大爷唤她“美”,这是我们当地对母亲的称呼。干人是刘大爷唯一的儿子,比我大不了几岁,却是全生产队中,我最亲近的人。一来我家和他沾点亲,二来他喜欢带我玩,最最重要的是,他掌管着喂养生产队一群牛的“大权”,格外令我神往。
干人,不知他名字由来,确实长得很干,瘦得像根灯杆,高出我一大截。那时,每家有任务,给生产队交喂牛草。母亲把这事交给了我。我每天放学后丢下书包就得背上背篓割牛草去。常至暮色时,才能把青草蓄满背篓,再送到牛棚,排队接受干人的过秤、登记。然后再摸着月色赶回家做作业,往往要熬到深夜。
他比我大几岁,已经是生产队的正式社员了。之前,我和他并没有一起耍,是去交牛草才和干人好上了。我那时“业务”不熟,不论什么草都风卷残云砍伐入篓,却不知野草是有种类之分的。有的草不仅没有营养,甚至还可能有害于牛犊。我把背篓放到他面前,他一边弯腰翻弄我背篓里的青青绿绿,一边说:“割草是不是没得上学安逸呀?”我没接他话,只盼他快点给过秤。他直起腰,手上拎起一大把,用力砸在地上,狠狠说:“你是要害死牛吗?”原来我把有毒的草也割来了。我被他吓着了,怕得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。见此情形,他像是倒被我吓着了,连忙说:“莫哭莫哭。明天来,我带你去学割牛草。”说着,从一旁的一个大背篓里捧出一堆青悠悠的鲜草放进我的背篓,再过秤、登记,总算交了差,完成了任务。
此后,我放学后就先找干人。他总在望乡台上牛棚里,不是在给牛洗澡,就是在给牛喂草。
然后他带着我,教会了我辨识各种可以喂牛的草,诸如甜象草、狼尾草,菊苣、巨菌草。“最好的是黑麦草,只是我们附近的地里很不容易找到。”我好奇的是,干人没有上过学,竟然有这么多知识,而且他的割草技术也十分厉害。
最关键的是,我能够早早完成牛草任务,早早回家做作业了。那些年里,我没有因为割牛草而误了学业。我也因此考上了城里的中学,考上了师范,再也不用像干人那样,在望乡台里守牛棚,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子了。
自从离开了老家,就没有看到过干人了。父母来城里,偶尔从他们口中听到他的消息。那个比观音还老的太婆活到了近百岁,死后埋在望乡台上。前两年刘大爷也走了,也同样没有走出望乡台。生产队散了后,牛棚也拆了,刘大爷的小坟就在牛棚的位置。干人找了个贵州媳妇,小日子没过几年,媳妇却跟人跑了。干人去找她,也离开了望乡台,一走好多年。回来时,庙宇改成的旧房子也破得不成样子,像他那灯杆似的修长腰身,被扭曲得零零落落。
但他的腰没有折,骨头依然很硬。他不仅重修了旧房,还把两个老人的坟打了墓碑。
去年秋天,我回了趟老家。开车行驶在新修的乡村公路,蜿蜒而登临望乡台,直达牛棚的位置。之前牛棚周边那一片荒地重新绿油油了,成熟的桔子挂满枝头,像是挂在望乡台上的小灯笼。
我从车窗望出去,看到一个老人在采果。他站在梯子上,背着竹筐,右手握着剪子,胡子稀疏,脚上踩着厚厚的布鞋。我认出了他,下了车,他也看见了我:“崇伟好久回来的?”他利索地从梯子上下来,挑了几个大的果子给我。
我们聊了一会儿,又上了车。他站在路边,一边向我挥手,一边嘱咐我路上慢点开。点了油门,车子启动,后视镜里,干人越来越小。当我拐进主公路时,干人,干人的牛棚,望乡台上那整修得气派的老房子,连同房子旁边的两个小土堆,都从后视镜里消失了。
施崇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