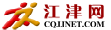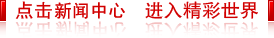泉水叮咚凉水湾
施崇伟
春节,回到麻柳,去看望长眠在鹤山坪的外公、外婆和舅舅。坟上,芳草萋萋;周边的田园,麦苗吐青,菜花醉黄。山野间,一条乡村公路通达四方,一座座砖房洋楼拔地而起。唯一不变的,是那笼幽幽翠竹掩映的凉水湾,那汩汩清澈的泉水依然不息流淌。
小时候,我每年都会来鹤山坪。外婆家老屋的背后有一条翠竹和杨柳簇拥的幽径。树影婆娑间,有叮咚泉水响。几块圆硕奇石留出一条窄缝,阴凉,清爽,里面藏着一口古井。井是天然的,无凿石之痕,无砌工之艺,圆乎乎的水面,长年平至井口,像一面镜子,映出四周的草色、树影。时常水面飘着一两张或青或黄的叶片,与杂乱的虫鸣鸟语,一起浮于镜面,一切都是清幽幽、亮堂堂。
这里就叫“凉水湾”。可以说,是凉水湾那口古井的水,把我喂养成人。
外婆的村庄,叫“砖房”。村落几十户人家,百十来人口,全都吃这口井的水。
幼年时,我喜欢跟着舅舅去挑水。往往是一大早,晨曦微露,天色尚早,我就跟在挑着水桶的舅舅身后出发。他的水桶在前面晃荡,我的影子在他身后追逐。走过石院墙,走过小石径,沿路是茂密的竹篁、槐林。蜿蜒而至谷底处,一棵挺拔的椿树从林中耸起,三四丈高,枝繁叶茂地撑出一把大伞。树下两块圆石之间留出一道狭路,通向水井,只够一个人、一挑担通行。
一条水线,源源不断,滴落而下,叮咚,叮咚,奏出清新的晨曲。圆圆的井,已蓄满清泉。舅舅把水桶放到井沿,而我,已趴下身子伏在井口。挑水的人,来挑水时,都是这样,先趴下身子,掬一口清泉,既解暑渴,也洗肺肠。其实,更像一种跪拜的仪式,是一种虔诚的感恩。
舅舅喝足后,蹲下身,一瓢一瓢地舀着凉水。水桶满上了,水挑在肩上。弯弯的扁担,两头垂下来的铁钩上,两只水桶随着他轻盈的步子,摇摆在凉水湾晨光铺满的小路。等井水蓄满水缸,一天的日子便觉得踏实而滋润了。
凉水湾的水可养人了。渐渐的,我喝着这里的泉水长到十来岁时,也感觉身上有了力气。便闹着,也要去挑水。大人挑水的桶,桶绳长,我够不着,水桶大,我挑不动。外公有手艺,便专门给我打了一挑小号的水桶。当桐油刷得锃亮的一对木制水桶做成后,我乐得起了个大早。我挑着水桶,奔跑而往凉水湾。打满水后,沉甸甸的担子压在肩上。我咬牙挑起,水桶却不那么听使唤,一路上晃晃荡荡,凉水溢出水桶,打湿我的裤子。本来满满的一桶水,挑到水缸前时,却也荡得仅剩小半。外公告诉我:这挑水啊,也是一门子手艺活。肩上的扁担要平稳,走路的步子要匀称。特别是在换肩时,一手轻扶扁担缓缓一抹,一手系紧桶绳平整一挪,那才能风平浪静,稳稳当当。
外公说这番话时,一脸严肃。我不知道,他是为我的无能在着急,还是为我把水给浪费了而心疼?
多年以后,我又回到鹤山坪,来到凉水湾。外公、外婆和舅舅,都已先后走了,而古井还在!他们葬在可以看得到古井的山坡上。我相信,地下的他们,仍能听见这泉水叮咚,仍能饮到这汩汩甘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