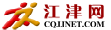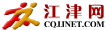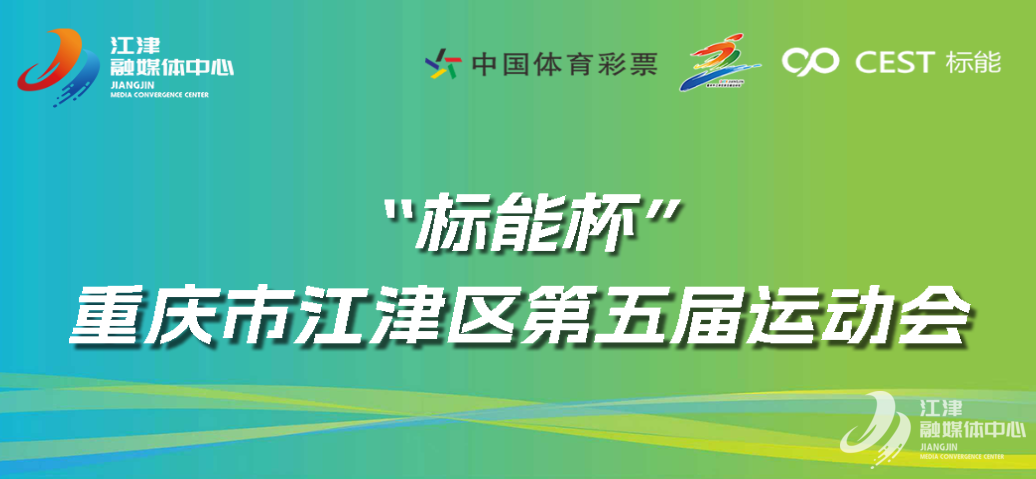山歌吼亮岁月

黄海子
李市镇人,如果不会“吼”两句山歌,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江津李市镇的人。李市镇的人,吼山歌这门技艺,仿佛与生俱来就在他们血液里流淌,只要找到出口,就会随时喷发而出。
我是李市镇人,随口也会吼两句山歌。
李市镇人一直把“唱”山歌叫着“吼”山歌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一个陌生人,走进李市镇地界,延绵不断的庄稼地的绿,像缎子一样铺陈在眼前;天空里飘着的几朵云,悠闲得像坐在自家门口歇气的汉子嘴里吧嗒出的旱烟烟雾;斑鸠咕咕地叫,燕子斜飞在绿色的地面上剪裁着风……
突然——路上的大哥喂/你要去哪家/这条路上的人家喂/没有我不知晓的哟……一阵山歌,像被惊吓的鸟从一片绿里直冲而出。那声音干净洪亮,又婉转随意,有些像陕北的秦腔,但更多的像一棵在一马平川里突兀出来的大树,直直的。不管从哪个方向,只要朝着树,远远就能望见。这棵树就是李市镇地界上的山歌了,而直直的站立着冲天的姿势,就是我们的“吼”了——一出声就气势足够,而且调门高亢,声线刚亮,率直的同时却也枝枝蔓蔓。
李市镇的人喜欢过两个节。
一个是过年,过年了,所有头年的晦气似乎都烟消云散,美好的希望和喜事都在前头。而此刻,家家门前都亮着花灯,灯光里,每一丝光亮都闪着喜庆。更别说艺人们的杂耍,灯戏等玩意在年里的祝愿和闹热了。
再一个就是端午。
一到端午这天,四村八乡的人们,像涨的端午水,从各个渠道里,汇涌到镇上。镇上的大街小巷,到处都是攒动的人浪。人最多的地方有两处,一处是看划旱龙船的,另一处就是看吼山歌比赛的场坝了。
场坝很大,能容纳上千号人。场坝的正前方,是一个很早以前遗留下来的老式戏台。端午这天,场坝就像起着风的大湖,人们在场坝里,就像被风卷起的浪,涌着,攒动着。而戏台,就像被浪花簇拥着的一座岛屿。
戏台上,摆满了乡人们认捐的“彩头”——有粽子、草帽、斗笠、鸡鸭……乡人们公推的评委,则坐在戏台的两边,手里拿着纸和笔,只等台下自愿上台吼山歌的人上台一吼,来人吼完,评委们评出好坏,吼得好的,去取贵重一点的彩头,差一点的,也去拿顶草帽或摘几个粽子,以示鼓励。
上午九点左右,只听三声锣响,吼山歌比赛就开始了。锣响声落,有按捺不住的,快速奔上戏台,对着人群一个鞠躬,扯开嗓子就吼起来。那时,乡镇上极少有送话器扩音器之类的扩音设备,所以声音大小全凭个人嗓子。
嗓子好的,一张嘴,整个场坝即刻就安静下来。只听那嗓子里即兴出来的调子,像大热天里吹来的一阵凉风,让场坝里的每一个人,都感受到惬意。如果是调门高亢热烈的,那就是过年时置办的杀猪酒了,每一个吃席的人都被佳肴和酒上了舒坦的醉意,全身都感到通泰和热络,也感受到了劳作过后的丰收和乡里人家热烈的盛情。
李市镇吼的山歌,除了几个调门,如:“跑山调”“水水调”“平路调”等,吼山歌的人除了遵循调门外,吼的歌词基本是无章可循的。它们的内容,皆是百姓随口从心而出的,吼山歌的见什么就吼什么。看见一棵树,喜欢了,张嘴就来:这棵大树哦/长得好伸展/传说的潘安耶/见着也要红脸……
这年端午,我二十出头的幺叔,跑上镇上场坝的戏台,用跑山调的调门高亢着吼了一段:台下的幺妹啊/好像天上飞的凤凰/我张望你飞翔的影子呀/张望断了我的颈子哟……幺叔在台上卖弄,台下外村有个姑娘,心思就被幺叔带走了,等幺叔吼完山歌,拿了彩头,下得台来,那姑娘就挤过来挨着我幺叔,后来就成了我幺婶。
那天,我老家的发小打电话给我,问我端午回不回老家看吼山歌比赛。接电话时,我正在阳台上打理花草,嘴里哼着:喝茶就喝茶呀/哪来那么多话/我的那个妹妹呀/她在打理我的家……我停了哼哼,回答发小:“一定回来,一定回来,我还想上台去吼几声。”
发小在电话那头笑。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