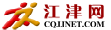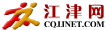曾冬的小渔船
施崇伟
我家门前有条小河,瘦瘦窄窄,清清澈澈。河码头边,常泊着一条小渔船。长梭梭的,浮在水面,风轻轻来,船轻轻漾,像一条大鱼,起伏着深呼吸。一根细缆牵着,荡开后,又漂回来,那份牵挂,像我对家乡的感情,久不久,就会回来看看。
站在岸边,望及河边,眼睛里像渗进沙子,目中所及之物感觉异样。河埠头缺了个口子?水位高低不平地倾斜?定睛分辨,哦,是小渔船不见了。
此前也常有不见小船的情形,一般是晨起时,那时,曾冬早已起身,划向下游更深的水域,撒网捕鱼去了。
曾冬是邻居。他老汉和我爹是儿时同桌,我们虽算是世交,我却比他大出十岁光景。我上师范时放假回家,总能在小河里见到这个“浪里白条”。等我成家后再回故里,他已成当地有船有证的正式渔民。
曾冬和小渔船的忙碌在早晚。
傍晚,是一天劳作的人们的闲暇时分。村民们端着茶壶,或烧着纸烟,在院坝里闲淡地说着春播秋收,或张家女出阁李家猪下崽。曾冬却没有功夫应付闲聊。他长篙一撑,小船利索转身,便向着河下游的深水处驰去。我在岸上望着,像望着一片悄然而去的树叶,在金色波浪中摇摇晃晃,一会儿就没了影子。那是捕鱼撒网的最佳时间,仿佛农民处于雨水时间的插秧播种,误不得时节。等他撒网归来,各家烛火已剩余烬。他却吆喝着,来二两酒,暖暖身子,消消寂夜。
待到天明,便迎来了捕鱼人的收获时分。小渔船沿着头晚上的水路驶去,虽然网在水下,捕鱼人熟稔每一个网格的方位与深浅,也清楚不同时节、不同水域,有不同的收成。好像鱼儿是他自家养的牲口,胖瘦、长短都在预料之中。所以,哪家来了客人,想要水蜜子,哪家要去城里走亲戚,想捎上一条河鲤,头天都可以向曾冬预订。他能很有把握地告诉人家:“明早八点来取!”
果然,取鱼的守在岸边片刻,便能看到船影飘来。等船一抵岸,曾冬揭开船头的板子,舱板下的清水里活蹦乱跳,便分装进了袋子、水桶。有捧在手上的,双手紧抱着,不敢有半点放松。不然,鲜活的鱼儿可能会用力挣脱人手,狡猾地溜进河里,逃之夭夭。
有次,得到曾冬许可,我也曾参与过他的捕鱼。
等曾冬解下缆绳,我一步跨上渔船。船体太小,摇晃得厉害。蹲下身子,趴在船沿,鼻尖几乎触到了水面。曾冬不紧不慢,沉着地,一脚蹬向岸石,脚一收回,船利索地离岸,惊起潜伏在水草丛里的小鱼,朝霞映出它们金色的鳞光,向着四处迸射。
船儿摇摇晃晃,当驶到了撒网的沙沱子时,曾冬便停止了划桨,任船儿在水中漂浮。然后,他蹲在船头,捋到网线的头子,慢慢地往上拉网。我也靠近曾冬,帮着他拉网。左手右手交替,网线慢悠悠浮出水面。渐渐地,有水声哗哗,那是鱼儿在网上翻卷细浪。看,网出水面了,我俩用劲一拉,直接拉到船头的舱板上。绿色网线间,挤挤挨挨,蹦蹦跳跳,有草鱼、鲫鱼、撅嘴鲢鱼……有的我叫不出名。曾冬拉住网底,一股脑倒进盛有水的舱里,得水的鱼儿和得鱼的人儿,一样欢快。
这次回家,村里也没了从前的喧嚣,枯水的小河露出寂寞的石头。那条记忆中的小渔船哪儿去了呢?找曾冬问问去。红漆门上铁锁一把像闭口的老人。转身间,那熟悉的瘦削身影出现。
“你不打鱼了?”
“政府要治理綦河,不允许捕鱼了。”
“船呢?”我不禁为之着急,不捕鱼的曾冬,日子咋过呢?
“船被收了。被一条大船拉走,往大江而去了。”手向下游指去,脸上的微笑很平静。
原来,为了保护綦河生态,几年前就不再让捕鱼了。所有渔民都交船上岸,政府给另外安排了工作。曾冬去了工业园区上班,新学了烧电焊的手艺。难怪他的皮肤被熏得黑黑的,牙齿还是那么白,像河边的贝壳。
我怅然若失。递去一支烟,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失去了渔船的曾冬。
他摆摆手,没接我的烟:“这样也好,生态改善了,水更清,鱼更多,我们生活在河边的人,不是更好吗?”
没了渔船的曾冬,才不像我这般失落。
他开了门,拉我进堂屋。堂屋正中墙上,挂着他父亲的遗像。墙下有个木柜,严严关着。他走过去,打开木柜锁,小小心心地,取出一条长长的木板——船桨!
“交船的时候,我悄悄留下了它。”
这时,他伸手向我要了一支烟。然后,蹲在地上,大口地吸烟。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促膝长谈……